他讲的“缺德笑话”,妈祖审完都笑了

审视感贯穿着小佳的成长。因神经系统先天性疾病,他说话和行动都有障碍,常被他人注视,他从小害怕理发,身体总会不由自主地摇晃,高中时他想成为作家,正是想躲到作品背后,逃避人群与目光。
连他自己也没想到,多年后他做的就是审视感极强的工作。“这就像我身上有道伤疤,或者胎记,上台时我先把衣服掀开来,告诉观众这里有个胎记,他们就不会再聚焦那里。”
记者 | 谢无忌
编辑 | Felicia
题图 | 受访者供图
闽南地区庙宇林立,小佳从小便好奇:为什么向神明掷圣杯问事,所有的问题总要设计成是非题?圣杯一正一反为“是”,两反为“否”,两正则是“笑杯”——代表神明笑了,暂不作答,留有余地。
但遗憾的是,无论连续掷多少次笑杯,提问人原则上不能收摊,因为它从始至终都不是答案,除非人们已经求得了痛快。
小佳记得,去年脱口秀专场巡演前,暴雨中,他走进湄洲岛妈祖庙,将段子文档放在祭台前:“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,请给我一个圣杯”连续两次一正一反,神明爽快通过终审,专场名《反正》由此而来。
“反与正相互依存。脱口秀里也有观点冲突,如同一枚硬币,我们看到了正面,也允许它有反面。两个正面是笑,也与脱口秀里的喜剧节奏相似。如果把笑当成一个终选项,或许很多困惑都能迎刃而解。”

小佳去年的脱口秀专场《反正》。(图/受访者供图)
在深圳的一家咖啡馆的角落,小佳笑着跟我解释“反正”的用意,话里带有闽南口音特有的粘连感。他一边说着,一边缓缓地捻着纸吸管。
过往八个月,他用睡前和飞行时间,在手机上写下了八篇故事,结集成新书《蜉蝣直上》。书里的自我介绍一如既往地呈现着他的反差感——一个“只想当严肃作家的喜剧演员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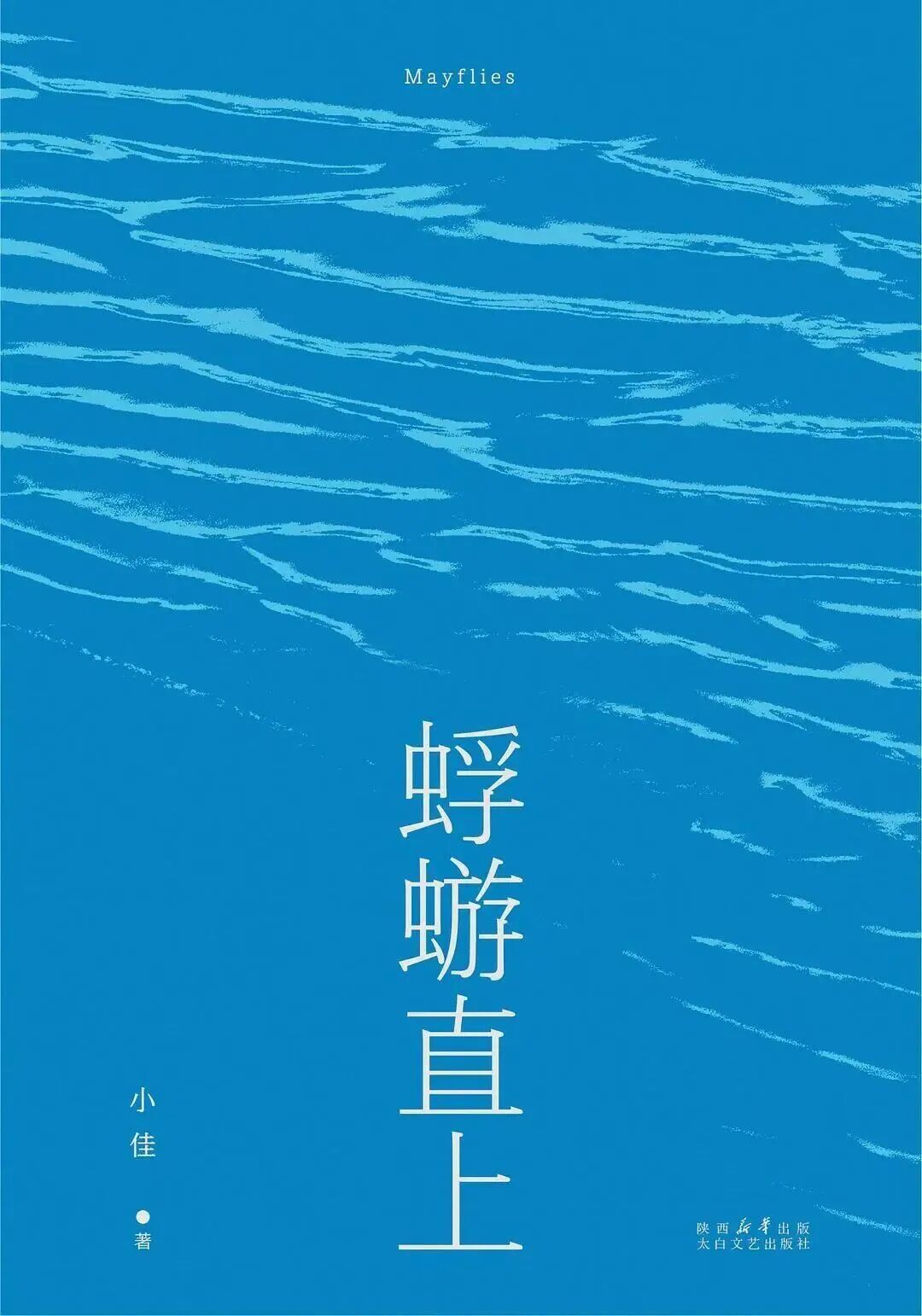
小佳 著
太白文艺出版社|果麦文化,2025-7-1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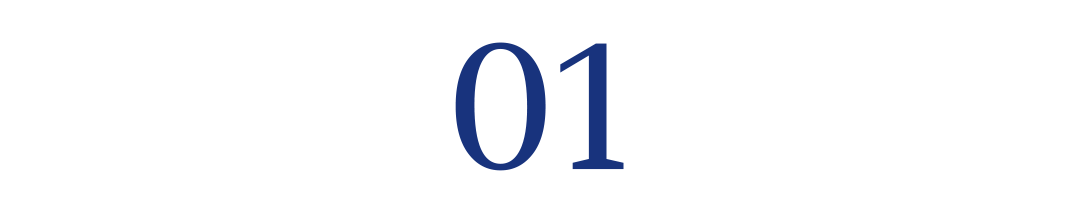
“审视感”
七夕当天,小佳负责一档喜剧线下恋综的主持。在现场,小佳问男嘉宾心仪对象的类型,对方说喜欢“做家务的女生”,台下哗然。小佳机敏接话:“除了做家务,还喜欢什么?”“真诚一点的。”小佳露出了狡黠的笑:“那就是要真诚做家务的。”台下笑声与掌声齐飞。
这是毒舌和辛辣的主持人小佳,也是台下许多女观众眼中贴心的男闺蜜般的存在。他善于读取气氛,调度言语和表情的分寸,一如他在脱口秀中惯有的喜剧节奏。

小佳在喜剧恋综现场主持。(图/作者摄)
散场时,几个奔着小佳来的读者托剧场人员请小佳在新书上写寄语和签名。在后台,小佳边用左手写着to签,边跟我打招呼,坦言自己在活动结束后不愿社交,仿佛一个“电量告急”的社恐I人。
随后,我们到了楼下一家咖啡厅。刚坐下来,他似乎为了暖场,主动找话题聊天,猜测我是不是湛江人,说我的口音让他想起了广西脱口秀演员梁海源。“我是广东客家人,口音这么重吗?”我笑问。“(口音)没关系,最开始李诞就是这么跟我说,你就放心说着自己的口音,那就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天生的标志。”他笑到拍掌,身体前仰后合。
等到我们的对话逐渐深入,他渐渐松弛,倚靠墙角谈起近日行程:每天见陌生人,面对审视仍然会不适。有一回在大理录制播客,他建议先聊天再录音,开始聊起了自己在大理旅游的见闻,让自己慢慢进入有安全感的状态。
审视感贯穿着他的成长。因神经系统先天性疾病,他说话和行动都有障碍,常被他人注视。他从小害怕理发,身体总会不由自主地摇晃。他记得理发师曾跟母亲轻轻怨叹。高中时他想成为作家,正是想躲到作品背后,逃避人群与目光。
连他自己也没想到,多年后他做的就是审视感极强的工作。“这就像我身上有道伤疤,或者胎记,上台时我先把衣服掀开来,告诉观众这里有个胎记,他们就不会再聚焦那里。”
2020年第一次登上开放麦的舞台,他发觉台下所有人的“审视”变得集中、自然。后来,在笑果训练营,程璐建议他换个视角看待身体缺陷。他从校园霸凌写起,发现观众并没有排斥,反而接纳。
这才有了脱口秀大会上小佳留下的金句:“我们都有病,只不过我的明显一点。”这句原为“我想跟这个世界说,你才有病”,经王建国建议修改了。小佳感觉自己从世界的对立面站回了同一边。
去年他与黑灯组合做了一场地狱笑话秀,演员互相吐槽,观众放下道德包袱大笑。他感觉被一种巨大的安全感包裹着。“舞台是一个安全的场域,我会默认他说什么都是安全的,默认看演出的人就是我的朋友。”
这种“说破无毒”的方式,是小佳面对审视转身为主导的姿态。在脱口秀创作上,他隐约发现了一种抵御审视感的武器——原本以为的那道“软肋”,只有当自己放下了,不再恐惧别人的审视和嘲笑,它才能在喜剧的处理下变成一块“盾牌”。

小佳说脱口秀时总是大笑。(图/受访者供图)
他学会了主动交底。如今每回理发前,他会先告知理发师:“我可能头会摇晃,不是为难你,是我身体的问题,不自觉会摇晃。”他发现当自己主动交出了把柄,反而能让自己放松接受外界的审视。
当然,“放下”仍是一个漫长的功课。“至今我还是会不自觉地观察别人投来的眼光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。”在采访间隙,他的话时而被周遭的声音淹没了一半。我凑近一些倾听,看到他时不时瞥向旁边客人的眼神,似乎在观察些什么。

山的压迫,海的平静
有读者说,《蜉蝣直上》像闽南版《俗女养成记》——有对故乡的温情细腻的回望,也有对活在世俗的锋利书写。
小佳对于《俗女养成记》中母女争执一幕印象深刻:小时候的陈嘉玲埋怨母亲严厉催促她上学读书,母亲哭诉:“你妈妈只上过国小,连ABC都不认得。要是我有得读就不用外出当女工。”陈嘉玲这才知道父母隐瞒学历是因为“怕丢脸”。
这段对话让小佳觉得编剧仿佛“在他家装了监视器”。小时候的他与父母的生活日常,也是包裹着话语的刺。他曾对着洗衣池边上的母亲吼:“要是养我这么丢脸的话,当初我生下来就把我弄死算了啊!”

小佳的老家房子。(图/受访者供图)
小佳笔下的闽南生活务实而浪漫,也有残酷窒息的家庭权力秩序。奶奶是童养媳,她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家庭地位,奶奶对家中男性的苛责逆来顺受。小佳从小就在这种氛围中长大,“看着我爸对奶奶大声呵斥,我从小也习惯这么对着奶奶,这种感觉无限循环。”
小佳的父亲有着典型的闽南父亲形象——在机关大院工作,热衷于维系世情关系,逢年过节张罗亲戚朋友的聚会,但在家里是一副“大男子主义”做派,因为儿子的病情而终日酗酒,对着妻子责骂、施加暴力。
小佳的母亲个性刚强,虽然在家庭当中承受了很多苦难,但她并不像奶奶那般忍让。她制止小佳父亲领养女儿,拒绝给孩子办残疾证再生二胎,因为她不想给儿子打上这个标签:“我儿子再怎么样,在我们心中,他就是正常人。”
小佳眼看着母亲投身于保险销售行业,从主任升经理,从一个家庭妇女变成了事业女性的角色,“她自己杀出了一条血路。妈妈也是我生命中见过的,第一个独立的女性”。
但小佳觉得,她并非完全的“独立女性”。他察觉母亲在某些方面思想依旧保守。同样经历了家暴后,从家里出走去广州打工的舅妈,连过年都没有回家。小佳的堂弟带着舅妈到张家界旅游,留舅舅一个人在家。这时候小佳母亲站在了舅舅一边,埋怨小佳的堂弟落得舅舅一个人在家冷清地过年。“她依然会站在家人那一边,难以站在舅妈的处境理解。”
这就是真实世界的复杂。小佳在书里提到的二姑和萍的故事,某种程度上,她们与当下主流的“从农村出走的女性”叙事不同。
二姑是小佳直系家族中唯一至今还留在故乡的女性。她是一个田地里长大的传统女性,从小被困在传统的家庭秩序里。但她是清醒的,不服输、不认命。在女儿与窝囊女婿鸡飞狗跳的婚姻生活里,她坚决维护女儿的利益:“男人家爱造的孽,凭什么苦的是女人。”
萍是小佳生命中的挚友。萍不顾家人反对,为爱远走高飞远嫁秘鲁。但是,萍的女儿出生后,便待在娘家由萍的父母照顾。他们每天跨国视频通话,然后有一天,萍好像突然理解了当时自己执意漂洋过海时,父母那份妥协里的不舍。
“如今她把女儿接到了秘鲁读书、生活,昨天还发了一家三口坐在沙发看电影的照片。”小佳在萍身上看到了勇敢追爱、不被闽南传统家庭困住的形象。小佳补充了一句,“故事是流动的,可能若干年后我写萍又不一样了”。
将镜头锁定在这些女性身上后,他跟出版社编辑坦承了自己的担忧,“她们都没有现代女性的思想观念,我们家乡更多的是不能完全走出来的女性,她们可能不看脱口秀,很多思想观念是滞后的,但这些都是真实的。”当时编辑看完鼓励小佳:“世界上不应只有一种女性,写出来才有一部分女性看见和关注到另一部分的女性。”
这些并非扁平单一的个体叙事,构成了复杂多面的真相,如同他在书中写到的闽南——“故乡大抵是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,它都会晚到几步的地方。”

小佳最近回了一趟老家,这是当时拍摄的图片。(图/小佳微博)
地缘与成长,水土与观念,闽南原住民环环相扣的地域文化,影响着小佳对具体生活的理解。闽南山与海殊异,连掌管山与海的神明也不相同。他回看自己三十年的成长弧线,刚好是前二十年长在漳州的山里,后十年活在厦门的海边。
去年他搬到了厦门岛外,房子与大海紧邻,从厨房、客厅到卧室,180°的海景视野。每天早上起床,他都会看到太阳从海边升起,阳光打在客厅的地板上。
“我很喜欢海,海广阔静谧,你总感觉可以静静跟它相处。山是一种压迫,闽南的山上总会藏着庙,人总会爬到山顶上拜拜。你会感觉不自觉要交代或者袒露些什么。”他说时手总会比划,但眼神坚定。

蜉蝣是一种可能会飞的生物
“蜉蝣”的书名来自一则科普视频。看完那个视频他突然觉得蜉蝣太有意思了,特别像人的一生。“它是一种寿命极短的昆虫,在水里经过数年的蜕皮,等到跃出水面就是最高光的时刻,接着便进入生命的倒计时。高光时刻转瞬即逝,它用一天完成了精彩的一生。”
在小佳看来,“直上”是灵魂越过沉重肉身,轻盈涌动的状态。但“直上”后便是“顺流而下”,是人生无常,也是一种生命的常态。

小佳之前住的厦门河南村最近在拆迁。(图/受访者供图)
他想起了父亲的猝然离世。“按照生命密度来说,他是丰富的。他在工作岗位上自己最有用的时候离开了,生命急转直下。我会幻想如果他还在世,有可能我们会在他的老年的阶段修补父子关系,但这就是遗憾,我无法预料人生。”
2019年父亲在下班途中去世。次年中秋,小佳在厦门的家中收到一袋柚子,那是父亲生前托人待到柚子熟后寄去他家中的。清明节那天,他把这个写进了段子:看到这袋柚子,想起了“欲言又止”的父爱。
闽南人自有与亡者日常交流的仪式——掷硬币,与掷圣杯同理。小佳与母亲常掷硬币问父亲是否吃饱了。一次母亲佯装不耐烦地说:“我去问你阿爸吃饱了吗。我问他,他就一直笑。”小佳听到,也笑了,“那个瞬间的场景还挺魔幻的,好似我们一家三口从没有分开过”。
母亲至今还会跟来客吐槽父亲,“走了6年了,但我妈讲这件事还会具体说到哪个情节,比如老是爱面子、喝醉酒,那个口吻就跟提到昨天晚上喝酒的阿爸一样。”

厦门的海。(图/受访者供图)
他在书里写下了一个带着无数缺点的闽南男人的一生。在一次签售会上,一位读者问:“随着父亲离去,你还有恨吗?”小佳顿了下:“更像是怨吧。一个人取得的成长,跟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影响程度是成反比的。”
另一位读者发现:哪怕他再坏,小佳笔下从头到尾都称他为“父亲”,而对于堂姐夫,他直呼其名——如果真正厌恶的话,他大概会用“那个男人”指代父亲。
小佳听完起了鸡皮疙瘩,被这个细节震慑住了。他才发现,哪怕不想粉饰父亲任何好与坏的行为,竭力客观,但真实情感仍不自觉地流露在字里行间。
最近他回到老家,看到客厅里有张低矮的塑胶椅,倾斜着正好面对着电视那面墙。他脑海里浮现了父亲看电视的身影。他原想赚了钱,就给父亲买一把太师椅。
“蜉蝣直上”一面是遗憾,另一面如同它的英文“mayfly”——可能会飞,代表了生命涌动的光芒。
时过境迁、物是人非的还有这一幕:时隔16年他回到初中母校,想起了曾躲在角落遭受过霸凌的自己,那个叫张佳鑫的男孩。
“一切都没有变,一切又好像变了。”这所母校的教室的桌椅不见了,黑板笔迹却没有被腐化掉。初中校园时光留给张佳鑫的是一个美好的转折点:在这里他遇到杨老师,鼓励他竞选班长,给予他面对生活的勇气。她也曾告诉张佳鑫:“你就是个追风的男孩,跑到哪里都是对的”。

小佳回到初中母校。(图/小佳微博)
那天恰逢下雨,他站在走廊边上伸手接雨,想起了小时候的张佳鑫的画面——以前放学下雨,很多同学都会有父母送伞。但张佳鑫知道,哪怕下雨天没带伞他也可以自己骑单车回家,雨太大了就找个旮旯,等雨小了就迎着雨回家,回到家父母就让他赶紧洗个热水澡。后来他学会了总要带一把伞在身上。
“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他们不爱我的体现,而是他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我,外面经受的风雨都是自然必经的过程,我可以独立面对。”

“我还是会羡慕”
“以前觉得登顶伟大,现在觉得和好友一起下山也很浪漫。”这是小佳在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第二季的淘汰感言,也可能是在脱口秀节目留下的最后的话。
“我明年不想再上节目,我想回到小剧场沉淀。”采访当天,他坦言自己有中度焦虑症,每天晚上失眠到天亮,自觉拧巴、内耗,看到了自己在事业上的企图心,但又感觉自己遇到了瓶颈。
“我感觉前几年走上坡路,可能是新人,怎么做都是往前的。近两年原地打滚,高不成,低不就,好像打破不了观众对小佳的固有印象。”

小佳在喜单节目中与星爷合影。(图/小佳微博)
当他看到身边同一阶段的脱口秀演员,有的夺冠,有的凭金句片段上了热搜,有天晚上他陷入了内耗,发了一条微博——“我还是会羡慕”。
这种失落感,如同每次演出散场后都伴随着他的、从人群回到个体的戒断反应。这两年他有了跨界的尝试,出演话剧《生之代价》、写书,毫不避讳“想红”的功利心,他需要曝光。办签售会,预期当天卖5000本书,结果只卖了1000多本。
他会翻看读者评论和演出repo。尽管随着时间推移,他逐渐学会面对外界各种不太友好的评价和审视,但他依旧觉得自己敏感易碎,会被这样的话刺痛——“为什么你舌头都还没捋直,就讲脱口秀?”“如果这么喜欢创作,为什么不在幕后?”
但他也警惕被人们冠以正能量励志的人设,他宁愿做“脱口秀小恶魔”——真实生活中的小佳喜欢挖坑,是朋友眼中“蔫坏蔫坏的好人”。他爱说地狱笑话,也希望观众哪怕“缺德”大笑,也不要被道德绑架。
“我不像头部演员,现在没有什么商务,但我有一颗往上爬的心,但同时我又自我警醒。我不知道成名给我带来的虚荣和满足,会不会让我脱离以前普通人的生活,忘掉原有的初心。我没有答案。”
小佳记得前几年参加商务活动时,品牌方会安排头等舱、豪华酒店。他一开始不好意思,后来逐渐变得理直气壮。一次商务出差,品牌方给许多嘉宾订了公务舱,唯独给他订了经济舱,他那一瞬间突然想要被公平地对待。但同时,他的“低配得感”又让他反省自己的欲望,“我一直在警醒自己,不要因为享受而变得慵懒,可人的劣根性总会在某些时刻冒尖。”
在这方面他承认自己拧巴,既有少年心气,不甘平庸,有想要红的野心;又希望自己能做到不再恐惧散场,哪怕被遗忘,也能重新回到小剧场,淡然接受散场之后的千百种或好或坏的人生。

比赛结束后,小佳回到具体的生活里。(图/受访者供图)
前几年的访谈里,小佳的故事是关于如何用幽默面对身体缺陷,面对“房间里的大象”。而如今这只“大象”可能换成了一种情感纽带的切断。比起死亡、衰老和遗忘,他更恐惧分别,尤其是在成长过程当中逐渐分离的状态,他害怕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后的羁绊,同样也害怕这段羁绊的突然消失。
最后一场脱口秀比赛,他试图用段子来消解掉某种不安的情绪。他讲了外婆在养老院的地狱笑话,幻想着未来一群好友摇摇晃晃地走着进养老院,“放眼望去,每个人最终都像小佳,身体都有组装的零件,一群人走着、走着,就散了。”
他曾在专场里讲过“玫瑰大哥”的故事:“玫瑰大哥”是他遇见的真实存在的一个人,有着文身,读书成绩差,但锄强扶弱——是小佳想象的、平行时空里的另外一个自己。
在专场最后,小佳虚构了他的故事结局——“玫瑰大哥”带着孩子,与小佳一同在庙里掷圣杯。小孩问:“小佳叔叔会好起来吗?”圣杯掉落,两个反面。小佳接过圣杯,把其中一个反面翻成正面,说:“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。”
